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之前,我想先做一个免责声明。
我写下自己的故事并非是想指责字母斯慕圈,或是挑战字母斯慕圈社群存在的合理性,我相信字母斯慕圈是人类性行为的一种合理表达方式,大部分字母斯慕圈社群也并非诚心想要去伤害加入ta们的人,但尽管如此,我依然受到了来自其中的侵犯和伤害。
2011年时我18岁,如果现在去回看那时的我,脑海里仅能冒出三个词语去描绘,“单纯”、“饥渴”、以及“无知”。
那时我刚刚解锁字母斯慕圈的爱好不久,就遇到了一位比我大了20岁的Dom,K。K是我们当地小有名气的字母斯慕圈社群组织者,许多圈内人对他的评价都一级棒,我通过他的网站和他取得了联系。
说实话,当他主动约我这个毫无经验的小白出去见面时,我觉得世界上真的有“撞上狗屎运”这一说。
见过几次面后,我开始相信“少女对于成熟且稳重的男人几乎没有抵抗力”这件事,很快陷入了对他的崇拜,许多夜深人静时的聊天里,我一边幻想着自己成为他的Sub,一边和他吐露自己的心声。比如我一直心心念念想尝试的SP,比如我自年幼时便常出现在脑海里的“强奸幻想”。
大概在我们认识一个月后,K向我发出了邀约,问我有没有空去参加他举办的社群活动。那时我已经去了外地上大学,刚刚军训完毕不久,找不到可以请假离校的理由,于是我向闺蜜坦白了一切,表示自己真的很想去,让她帮我想想办法。
“你确定吗?”闺蜜给我打来电话,“我觉得你最好别去,担心你的安全。”
但那时的我无知、饥渴且单纯,所以我斩钉截铁地跟她说,“我要去!”
K说那是一个关于SP的圈内聚会,大家会其乐融融地在一起讨论、交流SP的心得,也会有体验环节,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我是他的活动partner,那个找他去体验sp的人。
在我眼里,那是一个被许多人仰视着的人向一个小透明发来的真诚邀约,别说答应了,如果我有尾巴的话,当时一定都已经忍不住摇起来。
所以我和闺蜜说,我要去,有办法没办法都要去。闺蜜无奈,假装成我姐帮我骗过了难缠的辅导员。
活动是在一家酒吧的大包厢里,围坐了十几人左右,每个人的背包里都鼓鼓囊囊,在活动开始前不敢轻易拉开,像是藏着心事。
正当我坐在角落里局促不安时,K牵起我的手走向场地中间。他向大家隆重地介绍我,轻轻摸着我的头,说我是他的Sub。
在别人起哄、鼓掌、或投来羡慕的目光里,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件他单方面宣布的事情,其实他还没有征求过我的同意。后来我想起这事时才知道,他可能认为我答应成为他社群活动上的partner,就等于答应成为他的sub。
但那时我沉浸在虚荣心带给我的喜悦里,依偎进他的怀中,完全忽略了这一点。
聚会开始后,K教大家如何使用鞭子,大家起哄让K露两手,于是K转头问我想不想要体验一下,看我脸红,有人便又起哄说,K的sub都是很耐打的,小姑娘你行不行呀。
我当然行!我的脑子里没来由地冒出这样的想法。
于是K问我想要体验哪根鞭子时,我直接选了大家认为最痛的那条鞭子,任凭鞭梢雨点般落在我的背上屁股上,我始终一声不吭。
有几鞭子实在超出了我的忍受范围,痛到想骂脏话,但一想到不能给K丢人,我又连话带着舌头都吞进肚子里。
好不容易挨到K停下,我长长地舒了口气,K却走过来对我说,“我觉得你只是在忍耐,在配合,而没有真正地去享受这个活动的快乐。你要放开自己,真正地享受字母斯慕圈。”
许多人跟声附和,觉得我太拘谨了。
我有点被吓到,问K,“要怎么放开自己?”
K笑着摸了摸我的头,告诉我别担心,交给他就可以,他有办法。接着转过去和大家说,其实我有被强奸的幻想,一直想找个机会去实现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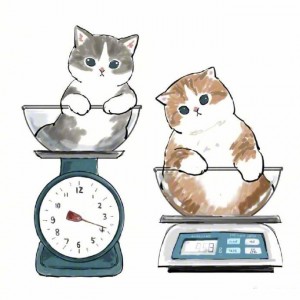
我的大脑听到这话瞬间空白,对着K和几个想走上前的人说我不要。他们愣了一下,但很快K又走上前来,直接撕掉我的内裤,拿着它向其他人展示了一圈,说,“你们看,其实她喜欢。”
我只好捂着自己,记得那时候我一直发抖,但想不起来为什么没有反抗,也许是我被吓傻了,整个过程中我都木讷而僵硬地呆在那里,任由K在我身上做着没有征得我同意的举动。
很快我感觉到有人抓住了我的手,有人压住了我的腿,有人在摸我的屁股,还有人扯掉了我的衣服。我惊慌失措地大喊大叫,但很快又有人捂住了我的嘴。
我听到有人说,“你们看,她真的喜欢,她都湿了。”接着便感到有什么在我的下体摩擦。
那一瞬间,撕心裂肺的疼痛让我翻转、挣扎、踢腿、咬人,现场一片狼藉,一片混乱中,K终于出面制止了我和其他人,说,“够了够了,意思一下就行,你们别太过分了。”
他们松手后,我抱着自己的衣服冲进包厢的厕所,发现自己的下体正在流血。我躲在厕所里,手指在110的按键上停留了好久,但最终没有勇气拨出去。
我觉得自己是个懦弱的人,我既不想欺骗自己,帮K对我造成的伤害找理由,又不想去承认自己认定的人,自己无论如何想参加的社群活动,给自己带来了任何的不适。
一旦承认了这一点,我便觉得自己很愚蠢,我便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所以我告诉自己:我必须是快乐的!我一定是自愿的!
于是我擦干了眼泪从厕所出来,回到K的聚会房间,他们大部分人都正面面相觑不敢说话。我端起一杯酒喝下去,对他们说,“别这样!我是自愿的好吗?我刚才拒绝了吗?没有吧?K不是都说了我喜欢这样吗?你们别大惊小怪的。”
说完我又拿了许多酒,但我不想再坐回K的身边,只想一杯一杯地喝下去。
为什么离开
很晚的时候闺蜜打来电话,问我活动的情况如何,我裹着被子整理了一下情绪,跟她讲述了一下刚才的过程,并告诉她,“活动超酷的!我很喜欢。”
“你确定吗?”闺蜜问我,“你听起来有点不对劲。”
我重新伪装了一种语气,和她讲,“哪有,活动真的很棒,K的那种统治力还有风度,完全就是我幻想中的Dom,聚会上的那种氛围也是超出我预期的,我体验了各种各样的SP,超级爽,非常适合我这种喜欢新东西,喜欢冒险的人,你这种良家乖乖女还是不要来啦。”
我一边极力掩饰自己的焦虑感,一边暗示闺蜜不要来参加类似的聚会。
电话挂断以后,我躺在床上,感觉自己正在试图与自己割裂,一闭上眼,就有一个声音在脑海里质问自己,我怎么会这么傻?我怎么会这么简单地就被伤害?我一定比这更聪明,我一定是自愿的!
就这样,一个自己试图用谎言说服另一个自己,最终把我撕裂。从K的聚会回学校后一个星期,我患上了严重的PTSD和抑郁症,此后我花了5年时间来治疗自己。
在此期间,我去过许多城市,参加不同字母斯慕圈社群组织的活动,我试图向自己证明,像K那样的人和社群只是例外,大多数社群内部还是遵循“知情同意”规则的。于是我在许多个国内外的聚会、和社交活动上度过了夜晚和周末,我本想找到比K和他的社群更靠谱的组织,但却目睹了更多的违反同意的行为。
我曾经和一位男性友人一起去参加一个“shibari”(绳缚)相关的聚会,聚会上我的好友找到一个看起来很资深,也备受其他人尊敬的缚手,问自己可不可以体验吊缚。
那位缚手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将友人吊上去后,噩梦却开始。
那时刚好有人向该缚手请教鞭子的相关问题,那位缚手便顺手将我半空中的友人当成了教具,一边解答别人的疑虑,一边朝他的身上挥起鞭子来,友人并不想被打,却又因为没有约定安全词,只能在半空中疼得吱哇乱叫,央求缚手放他下来。
令我不解的是,在场的大部分人只是在我友人的哀求声中哄笑。
于是我站起来要求该缚手放我的朋友下来,他却自信地和我说,你朋友没事,他在上面舒服着呢。
事后我和我的友人都觉得备受侵犯,于是向该社群的管理者举报了这位缚手,认为他无视我友人的安全信号,对我友人的身心都造成了伤害,希望这位缚手可以对我的友人公开道歉,且让这个字母斯慕圈社群中的每一位成员都知晓此缚手在这一活动上的不当行为。
但这位管理者和我友人聊了许多次,都希望可以大事化小,不要闹大,诉说了许多自己的苦衷,希望我们接受私下道歉就好。
本来我们已经心软,但当我们看到这个社群的下一次活动,依然邀请了这位缚手作为嘉宾时,我们至此对这个社群不再抱有希望。
我们给社群里的其他成员群发了消息,跟他们说了我友人的遭遇,但令人心寒的是,大部分人都告诉我们那位缚手是一位技术和人品都很好的人,是我们太敏感了而已。
事实上这些事情正是我决定离开字母斯慕圈社群的原因,虽然几乎每个社群都把“自愿与同意”喊得响亮,但在我参与的实际的社群活动中,违反同意的行为却随处可见。
更令我感到心寒的是,许多社群内根本不认为这些行为是有问题的,他们觉得自己已经遵循了“知情同意”的规则。
比如上文中的资深缚手,他拒绝向我的友人道歉,因为他觉得我的友人同意被他吊缚,便等于同意了吊缚过程中他拥有自由操作的权利,他认为这是一个S的基本权力,否则叫什么支配者呢?
我觉得这主要是社群负责人的责任,他们没有统一社群内对于“安全、知情同意”的认识,没有让所有社群人员明确地知道他们认同的“知情同意”的边界在哪里。如果我和友人事先便能知晓此社群活动的边界与我们理解的如此不同,我们便完全可以避雷不去参加了。
2014年我去香港当交换生,在参加一次私密的字母斯慕圈社群聚会时,社群管理者安排了一位“监督者”,由完全不了解字母斯慕圈文化的香草人士担任,任何越界的行为都可以向他举报,由他去评判这样的行为是否违规。
由于这一角色不由圈内人担任,所以极大地避免了那些根深蒂固的社群内偏见,不得不说,这是为数不多令我感觉体验感较好的圈内聚会。
但据说这一制度后来遭到了社群内部的集体抵制,有人认为香草人士不了解字母斯慕圈人群的心理,自己的行为不应由他们评判,有人认为这是“独裁和暴政”,于是便换了“监督者”,后来又爆出监督者同某些主办人员沆瀣一气的丑闻,这一社群也就此沉沦。


